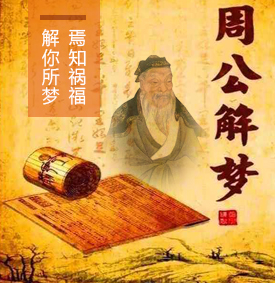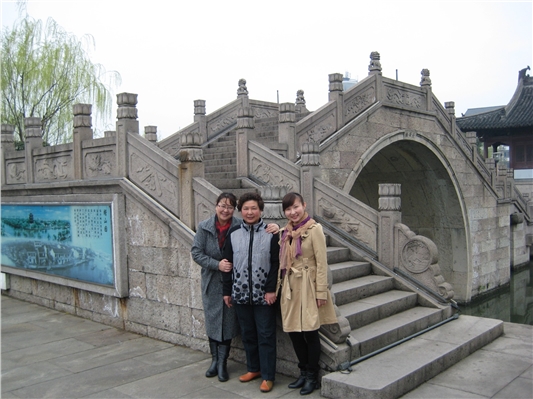明清时期陇东人口迁徙纪要
在黄土高原腹地,庆阳这座被子午岭与六盘山环抱的古城,自秦汉起便是中原王朝经略西北的锁钥之地。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时光里,一场场或主动或被动的人口迁徙,如泾河、马莲河的水流般浸润着这片沟壑纵横的土地,重塑着这里的族群构成、文化肌理与社会格局。迁徙的浪潮里,有戍边将士的铿锵足迹,有流民垦荒的艰辛背影,有商贾行旅的驼铃声声,他们带着不同地域的血脉与习俗,在庆阳的黄土塬上扎根、融合,最终沉淀为这片土地独有的记忆。
一、明代:军屯戍边与流民归聚,奠定族群新格局
明朝立国之初,庆阳所处的陕甘地区因元末战乱满目疮痍。《明史·食货志》载:“元末之乱,中原荡析,西北尤甚,庆阳一带城郭空虚,田野荒芜,户口十不存三。”为巩固西北边防、恢复地方经济,明太祖朱元璋推行“军屯”制度,将庆阳纳入九边防御体系的重要节点,一场以军事移民为核心的迁徙浪潮由此展开。
洪武二年(1369年),徐达率军平定庆阳后,随即下令“留军戍守,垦田自给”。大批来自江南、中原的卫所士兵被派驻庆阳,仅庆阳卫、环县守御千户所便屯驻军士万余人,连同家眷逾三万口。这些军士多来自江苏、安徽、山西等地,他们携带着江淮的稻作技艺、中原的农耕经验,在庆阳的川塬地带筑堡屯田。今庆城县驿马镇的“江淮堡”、镇原县的“山西庄”,皆是当年军屯移民的聚居地。堡内至今留存的族谱中,仍清晰记载着“洪武三年,自庐州府合肥县迁庆,屯垦于驿马关下”的字句;环县虎洞乡的张氏家族,其先祖为明初戍边的山西大同卫士兵,族谱中“携弓刀戍环,披荆斩棘,筑寨而居”的记录,印证着军屯移民的艰辛与坚守。
除军屯外,明代庆阳的人口迁徙另一主力是流民。明初朝廷推行“招抚流民”政策,对无地农民“给田垦种,免赋三年”。自洪武至宣德年间,山西、陕西关中、河南等地的流民源源不断涌入庆阳。彼时庆阳荒地广袤,马莲河、蒲河沿岸的川地尚待开垦,流民们“结庐为舍,烧荒垦田”,逐渐形成新的村落。今宁县早胜塬的“河南村”,便是宣德年间河南彰德府流民聚居形成;合水县太白镇的流民则多来自陕西渭南,他们带来的花椒种植技术,至今仍是当地的特色产业。
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庆阳的移民并非单向流入,亦有少量本地人口外迁。正统年间,庆阳遭遇连续三年大旱,“饿殍遍野,民多流亡”,部分百姓被迫迁往陕西汉中、宁夏平原一带。但总体而言,明代庆阳人口以流入为主,至万历六年(1578年),庆阳府在册人口已达12.6万,较明初增长近十倍,江南、中原、关中的文化因子在此交融,形成“堡寨林立,俗兼南北”的社会风貌。
二、明末清初:战乱流离与清廷招垦,人口的凋零与复苏
明末的战火,再次将庆阳拖入人口锐减的深渊。崇祯年间,李自成农民军多次转战庆阳,与明军、清军反复拉锯,“城郭数度易手,百姓流离四散”。顺治元年(1644年),清军入关后,庆阳又遭西北回民起义波及,史载“环县、镇原一带,村落为墟,人口亡失过半”。康熙初年,庆阳府在册人口仅余4.2万,不足明末的三分之一,昔日的屯田沃野再度沦为荒丘。
为恢复庆阳经济,清廷延续明代招垦政策,且规模更甚。顺治十年(1653年),朝廷颁布《垦荒令》,规定“凡流民垦荒,永为己业,六年后起科”,并鼓励地方官“招民垦荒,以招垦多寡定政绩”。这一政策吸引了大批山西、陕西、甘肃东部的百姓迁入庆阳。其中,山西移民规模最大,仅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便有近两万山西忻州、代州百姓迁至庆阳府属各县。他们多选择在明代军屯废弃的堡寨附近定居,利用遗留的水利设施垦田,今庆城县的“忻州堡”、华池县的“代州塬”,皆是山西移民的聚居地。
除汉族移民外,清代庆阳还迎来了少量回族移民。康熙年间,清廷平定西北后,将部分归附的回民安置于庆阳府属的宁州(今宁县)、环县一带,形成回民聚居区。环县甜水镇的回民村落,其先祖多为康熙末年从宁夏吴忠迁来,他们带来的牛羊育肥、皮毛加工技术,丰富了庆阳的产业结构。
雍正、乾隆年间,庆阳的人口迁徙进入稳定期。此时庆阳荒地已基本垦辟,移民开始向山区拓展,华池县的子午岭边缘、合水县的黄土丘陵地带,陆续出现新的村落。至乾隆四十年(1775年),庆阳府人口增至28.5万,恢复并超过明代鼎盛时期,族群构成也趋于稳定:汉族占九成以上,回族约占百分之五,另有少量满族(清代驻防八旗后裔)散居各地。
三、迁徙印记:黄土塬上的文化融合与传承
明清两代的人口迁徙,不仅改变了庆阳的人口数量与分布,更在文化、民俗、建筑等层面留下了深刻印记。
在建筑风格上,明代军屯移民带来的江淮民居特色与庆阳本土的窑洞建筑融合,形成“窑房结合”的独特样式。庆城县的“堡子窑”,外层为江淮风格的砖石堡墙,内层为黄土窑洞,兼具防御性与宜居性;宁县的“四合院窑洞”,则将中原四合院布局与窑洞结合,正窑为长辈居所,两侧厢窑为子弟住处,体现着中原的宗法礼制。
民俗方面,移民带来的习俗与本地传统相互交融。庆阳的“社火”中,既有陕西关中的秧歌、山西的旱船,又保留着本地的“跑驴”“铁芯子”;宁县早胜塬的婚俗,既沿袭河南的“拜天地、跨火盆”,又保留庆阳本土的“撒五谷、闹窑洞”;环县的饮食中,山西移民带来的刀削面与本地的荞麦饸饹结合,形成独具特色的“荞麦刀削面”,至今仍是当地的美食代表。
语言上,庆阳方言呈现出“杂糅南北”的特点。今庆阳方言中保留着大量江淮官话词汇,如“锅巴”称“锅粑”、“傍晚”称“黄昏头”,皆是明代军屯移民的语言遗存;而“圪蹴”(蹲)、“嫽扎咧”(好极了)等词汇,则来自陕西关中移民;山西移民带来的“俺”“咱”等自称,至今仍在庆阳北部乡村使用。
宗族文化的传承更是迁徙记忆的鲜活载体。庆阳各地的族谱、祠堂,多记载着先祖的迁徙轨迹:庆城县王氏祠堂的楹联“洪武迁庆,屯田立业;世代相传,不忘本源”,宁县李氏宗祠的碑文中“自晋迁宁,耕读传家,历十世而不衰”,无不诉说着移民对故土的眷恋与对新家园的坚守。这些族谱与祠堂,成为连接庆阳与中原、江南的文化纽带,也见证着不同族群在黄土塬上的融合共生。
四、迁徙之影响:经济重塑与社会变迁
明清人口迁徙对庆阳的影响,深入经济、社会的方方面面。经济上,移民带来的先进农耕技术推动了庆阳农业的发展:明代军屯士兵引入的水车灌溉技术,使马莲河沿岸的川地成为“旱涝保收”的粮仓;清代山西移民推广的玉米、马铃薯种植,让庆阳的山区荒地得到有效利用,至乾隆年间,庆阳已成为陕甘地区重要的粮食产区,“庆阳麦、环县羊、宁州梨”闻名西北。
社会结构上,移民的涌入打破了庆阳原有的宗族格局,形成“多族群混居,多姓氏共处”的社会形态。明代军屯移民的后裔多聚居在堡寨,形成以军事编制为基础的社群;清代流民移民则以地缘为纽带,形成“同乡聚落”,如山西移民多聚居于塬上,陕西移民多分布于川地,这种分布格局至今仍有迹可循。同时,移民带来的商业意识也推动了庆阳商贸发展,清代庆阳城内的“山西会馆”“陕西会馆”,成为商贾往来的枢纽,马莲河畔的庆阳府城逐渐成为陕甘边界的商业重镇。
文化上,迁徙促成了庆阳多元文化的形成。中原的儒家文化、江淮的水乡文化、关中的秦陇文化与庆阳本土的游牧文化相互碰撞融合,孕育出独具特色的庆阳文化。庆阳剪纸中既有江南的细腻,又有西北的粗犷;道情皮影戏吸纳了陕西秦腔、山西梆子的唱腔,成为中国皮影戏的重要流派;就连庆阳的民歌,也兼具中原的婉转与西北的高亢,这些皆是移民文化融合的结晶。
五、余韵:黄土塬上的迁徙记忆
时至清末,庆阳的人口迁徙渐趋平缓,历经明清两代六百余年的移民浪潮,这片土地早已形成新的族群认同。那些来自江南、中原、山西的移民后裔,虽仍保留着先祖的部分习俗,却早已将庆阳视为故乡——他们说着庆阳方言,吃着荞麦饸饹,在黄土塬上春耕秋收,将迁徙的故事化作族谱中的文字、村落里的传说。
如今,行走在庆阳的塬上川下,仍能触摸到明清人口迁徙的痕迹:庆城县的军屯堡寨遗址、宁县的移民宗祠、环县的山西会馆残碑,以及老人口中“祖上从山西洪洞大槐树下迁来”的讲述,无不印证着那段波澜壮阔的迁徙史。这些痕迹,既是庆阳人口发展的见证,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的缩影——不同地域的人们因战乱、戍边、垦荒汇聚于此,在黄土塬上扎根、融合,最终成为这片土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明清时期的庆阳人口迁徙,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画卷,记录着黄土高原的沧桑与新生。那些迁徙而来的人们,用汗水浇灌了荒芜的土地,用智慧融合了不同的文化,他们的故事,早已融入庆阳的山山水水,成为这座古城永恒的记忆。当今日的阳光洒在子午岭的林海、马莲河的碧波上,我们仍能从这片土地的脉动中,感受到六百多年前迁徙者留下的力量与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