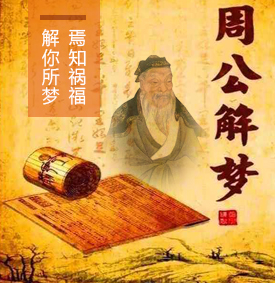我的爷爷李宗信
爷爷李宗信
发布时间:2014-02-28
爷爷李宗信,太康县符草楼镇李楼村人,太康李氏本支第二十世,生于1910年4月17日(庚戌年三月初八)。逝于1984年2月11日(甲子年正月初十),寿74。爷爷青少年时家道殷实,曾祖李玉珍为地方名医,在乡里有较高威望,明国初期还一度当过国民党的乡长,后因不谙官道又弃官重 操旧业。曾祖生三子一女,爷爷为长。曾祖在四十五、六岁时就因病去世了。之后,爷爷边务农边行医维持家境。爷爷在务农方面是村里人人敬佩的好手,但医术赶不上曾祖,行医也仅限于一些常见病的治疗和种牛痘。种牛痘在当时被称作“点疮子,”爷爷“点疮子”的足迹遍布周边二三十个村庄。“点”时不收费,只是在麦收后收一升麦子,少给也可以,不给也算了,不要第二次。爷爷和曾祖一样好朋好友,走到哪里朋友交到哪里,其中关系更好的换帖子拜金兰,关系特好的拿子女认干亲两人结为干亲家。朋友多了交往多,来往随礼吃喝招待成了家里的沉重负担,加上当时天灾不断、赋税抽捐名目繁多,以致家境日衰。1938年6月,蒋介石为了阻止日本人南下,在郑州花园口炸开黄河大堤,我们家这里顷刻间变成一片汪洋,村里所有房屋全部倒塌,老百姓祖祖辈辈积攒的家业瞬时清零。别无他法,爷爷只得用门板绑成筏子载着全家老少到地势稍高,没有被水淹的岳父家里暂住谋生。八年后黄水退去,爷爷回到“家”里从二尺多深的黄泥之下挖出部分砖瓦,和泥脱坯在原址盖起来三间草房,又在草房东山墙处斜搭一间小棚作为厨房,这样总算又有了全家的安身之处。
解放后,家乡进行了土改,我家被定为贫农成分,分得部分土地农
具,之后随乡亲们一起逐步从互助组过渡到人民公社。从那时开始爷 基本不再行医,一直在生产队里当“大把子”。当时人们习惯于把队里
负责驾驭牛马耕耘土地、拉车碾场的人叫“把子”,“大把子”负责管
理“把子”们并协助队长安排队里的耕种收割等事宜。当“大把子”要
求有高超的驾驭牛马的技术并且精通农时农技。耕一块地开始的第一犁
叫开墒,走在前头的牲口因没有犁过的地作参照而走不了直线,全靠
“把子”用口令和鞭子校正牠们的行走方向,我曾亲眼看到爷爷赶着牲口
在几百米长的地里第一犁就走出笔直的一条线,并且仅凭目测就能将整
个地块基本准确的分为等宽的两块或四块进行耕作。
爷爷要求自己的子女极严,经常教育父亲和姑姑们饿死也不准偷拿别人
家的东西,更不能偷盗队里的庄稼(因为那时侯经常挨饿);对人要有
礼貌,不要和邻里闹矛盾;谁家有困难能帮的一定要帮着点;做人要诚
实、守信,要对待起自己的良心;与人共事宁愿自己吃亏也不能让别人
看不起等等。我小的时候,经常听爷爷片片断断的给我讲《三字经》里
的故事,也时常因为坐姿不端、走姿不正,客人来了不会说话,或是吃
饭时用筷子在菜盘里乱挑乱翻,写大仿时握毛笔的姿势不标准等等受
到批评和指正。父亲也就是因深受爷爷的影响以至于在他当大队干部
随时都有机会贪点、占点时独善其身,差一点把我和二弟饿死。
爷爷幼时深受曾祖的教诲,心地良善,乐于助人,平时对人态度
谦和,礼数周全,但他性情耿直,嫉恶如仇,有时又刚烈得出人意料。
解放前本村保长——他的一个远房族弟带随从骑自行车在他面前经过,
因未下车说话,激怒了爷爷,遂飞起一脚将保长从车上踢倒在地,保
长站起只是尴尬一笑急忙推车走人。大集体那时候,哪个要想沾一点
队里的便宜,或是偷了队里的庄稼,如让他碰上定是不饶,谁也不行。
虽然不是干部,比干部管事还多,有一次我的一个堂叔在队里干活耍
滑,队干部管不下告到爷爷面前,爷爷教训几句,堂叔不服,爷爷手里
的牛鞭应声落到了堂叔的身上,堂叔吓得扭身就跑。即使是当时已经当
了大队干部的父亲,也曾因为在村里说了句什么不当的话而遭到爷爷当
众斥骂。
爷爷幼时读过几年私塾,文化程度不高,但交友众多,见多而识
广,天文地理风土习俗都能说出个一二来,在村里也算是比较有学问
的人了,因而村里不管谁家有大点的事总爱听听爷爷的意见,请他指
点或出面主持。谁家夫妻父子或邻里之间闹架,只要爷爷一出面说话
没人不听。爷爷粗通韵律,虽不识乐谱但能听音断位拉板胡,豫剧二
八流水各种板式唱腔音乐烂熟于胸。爷爷还精于厨艺,水平在农村属
于专业级别。爷爷能喝酒,划拳的水平也非常高,几乎没见谁赢过他。
爷爷烟瘾很大,一把旱烟袋从不离身,一抽起来就是连着几锅,直到
嗓子里不着的打起响嗝,才心满意足的收起烟袋去干活。他也因此患
上了支气管哮喘病,后来虽然戒了烟,但病情还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愈
来愈严重,到六十七、八岁时,爷爷就基本不再参加劳动了。
爷爷后来又患了前列腺炎,先是尿频,没引起他的重视,到了70岁
左右,病情发展到排尿困难,才说出来并到医院做检查,确诊后治疗效
果不很理想。那时我在重庆工作,还从重庆买些德国进口的前列康等药
物寄回家来。这样常规药物治疗时好时坏直到1983年底,病情发展已经
很严重,排尿十分困难,膀胱充盈压迫直肠,造成大便排泄也困难起
来。到县医院检查后决定作膀胱造瘘手术,但爷爷说快过年了,我在这
一住院大家都过不好年,等年后再说吧。结果在年前年后这一个月左右
时间里,由于大小便困难,爷爷尽可能的减少进食,再加上支气管哮喘
冬季表现更为严重,缺乏营养,供氧不足,身体很快就垮了,到春节后
再去医院治疗时,爷爷已经不能自己走路了。膀胱造瘘手术做的很成
功,通俗的解释就是从膀胱里插一根管,通过腰侧直接将尿液排出体
外。手术后第三天早饭后,爷爷突然对我说要回家,我和陪侍在侧的
一个堂叔都劝爷爷说先别回去,医生说还要在医院观察几天云云。爷
爷柔弱的声音里夹杂着酸楚,暗淡的目光里显露着埋怨:你俩咋恁傻
也!赶快回家。此时来陪护的亲属和来探视的亲友陆续到来,有年长
者看到爷爷情景不好,不再劝他继续在医院恢复,立即办出院手续,
将一张软床绑到架子车上,拉着爷爷飞奔回家,在路上我一直守着爷
爷,不时叫他两声,用小勺往他嘴里喂点水,但他答应的声音越来越
小,下午一点左右刚到家,爷爷便静静的、安详的离开了我们。时间
是1984年2月11日,农历正月初十。
爷爷和奶奶一生养育四女一子,大姑姑15~16岁时染伤寒病夭亡,
现在健在的大姑姑其实是二姑姑。奶奶也姓李,本县马厂镇挖勺李村
人,奶奶在农村妇女里算是高个子,身形脸型都偏瘦,背稍有一点弓
形,走路缓而步幅大,平时话不多,只是不停的干活。对人亲切而实
诚,对子女包括对我这个孙子要求都很严格,很小就让我帮她抬水,
虽然水桶基本就在奶奶的手边我只不过在扁担的那一头承担点点重
量,但4岁的年纪和奶奶的大步子还是让我受不了,不干也是要挨
“打”的。奶奶的过早离世完全是饥饿造成的,那时候吃大食堂,谁
家也不许开火做饭,发现谁家冒烟了干部们就会去搜查,一般性的处
理是没收食物,把锅拿去砸了,对个别态度不好的晚上开群众会斗
争。被斗争者在会场中间被周围的人推来搡去,这种形式被叫做“炒
蚂虾”。记得一次奶奶从娘家带回大致上有一斤红高粱,回家便装在
一个煨壶里埋在院子里一块洗衣服用的青石板下面。不知道干部们从
何处得到了消息,这边刚埋好他们便闯进家来,很快找到那个煨壶,
把高粱倒走后将煨壶摔碎走人。奶奶在一旁搂住我看着这一切一句话
也没说,可能是因为奶奶态度“好”,全家人一直担心的晚上的斗争
会并没有把奶奶叫出来“炒蚂虾”。我记得当时食堂供应的饭食实在
是太少了,有一次我去食堂领饭,全家8口人定量的生面条被饥饿难忍
的我在不到30米的路上吃掉了一半,到家后,看到小饭筐里仅剩的些
许生面条,全家人望着我,目光里埋怨、怜惜还有在眼眶里打转的泪
水至今令我记忆犹新。那时候,高粱糠,红薯藤,棉籽壳,玉米芯,
麦苗,榆树皮,几乎各种树叶,各种野菜,河里小到头尾相接的鱼
虾,耗子、蛇甚至屎壳郎都成了人们的充饥物,春天青黄不接之时情
况更为严重,奶奶就是吃了从地里捡来的硬的像劈柴一样不知哪一年
遗留在地里的坏红薯而得了肠梗阻,家里根本没钱治病,一阵阵的剧
痛使奶奶的哀号撕心裂肺,几次翻滚着从床上摔到地下……。弥留之
际,奶奶对父亲说:“孩呀!我得的是结症,不用给我治了,咱家没
钱……”。就这样,奶奶斜靠在父亲怀中,在全家人无奈而悲痛的目
光中,被病魔慢慢夺去了生命,年龄不满五十岁,时间是1959年春。
奶奶生前没有留下照片。